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及发展模式
|
钱敏(2001- ),女,安徽枞阳人,硕士,研究方向为城乡规划与人居环境。E-mail: 2023110514056@stu.cqnu.edu.cn |
收稿日期: 2024-12-09
修回日期: 2025-06-04
网络出版日期: 2025-09-28
基金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JYB0159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071217)
重庆师范大学校级项目(22XLB002)
The tourism symbiotic system and development model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Received date: 2024-12-09
Revised date: 2025-06-04
Online published: 2025-09-28
钱敏 , 张虹 , 戴技才 , 张慧玲 . 重庆市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及发展模式[J]. 自然资源学报, 2025 , 40(10) : 2735 -2754 . DOI: 10.31497/zrzyxb.20251010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is based on the symbiosis unit formed by the interdependence of elements between villages, in the symbiosis environment, with the help of a variety of interactive synergistic relationships and symbiosis modes of construction of the organic whole. It aims to integrate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promote village symbiosis linkage, and enhance the effect of regional tourism development. Based on the symbiosis theory, the article clarifies the three elements of the symbiosis system, such as symbiosis unit, symbiosis mode and symbiosis environment. Along the path of "tourism source-resistance surface-tourism corridor", the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is constructed. We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tourism resources, clarify the spatial patterns of different types of symbiotic systems, and propose a tourism development mode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re are 33 symbiotic units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with larg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value of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resources in different places. There are 21 high-value symbiotic units, accounting for 63.63% of the total, which are mainly distributed in the southeastern mountains where minorities gather. (2) There are 83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corridors in Chongqing, and the average value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maturity score is 0.068, show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West Chongqing>Northeast Chongqing>Southeast Chongqing". (3) The symbiotic systems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in Chongqing are categorized into cultural heritage type, ecological landscape type, and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type, accounting for 59.04%, 14.46%, and 26.51%, respectively. Each type of system makes full use of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natural landscape and minority culture, farming culture, etc. to enhance the development capacity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and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The innovative contribution of this study lies in constructing a symbiotic system for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based on symbiosis theory. It successfully solves the problem of isolated tourism development among traditional villages. It provides an important reference and methodology for comprehensively integrating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resources, constructing a new pattern of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promoting diversified and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表1 数据来源Table 1 Data sources |
| 数据名称 | 来源 | |
|---|---|---|
| 国家级、 市级传统村落 | 村落年代、面积、民俗活动、特色美食、非遗文化传承人数、少数民族种类 | 中国传统村落网(http://www.chuantongcunluo.com/)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https://www.dmctv.cn/) |
| 建筑功能、形式、建筑材料 |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 |
| 自然地理 环境数据 | DEM | 地理空间数据云(https://www.gscloud.cn/) |
| 年均气温 | 重庆市气象局(http://cq.cma.gov.cn/) | |
| 地质灾害危险性 |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https://ghzrzyj.cq.gov.cn/) | |
| 植被覆盖率 | 地球资源数据云平台(http://www.gis5g.com/) | |
| 生境质量指数 |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https://www.resdc.cn/) | |
| 人文经济 社会数据 | 重庆市行政村边界数据 | 地理遥感生态网(https://www.gisrs.cn) |
| 人口数据、人均GDP、 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 第七次人口普查 《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乡镇卷)2023年》 | |
| 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高保护等级 | 中国民族文化资源库(http://m.mzzyk.com/) 中国传统村落数字博物馆 | |
| 村落所属的类型、文化区 | 参考文献[22] | |
| 村落所获的文明村镇、 重点旅游村、 美丽宜居村庄等荣誉称号等级 |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官网(https://nyncw.cq.gov.cn/) | |
| POI点 | 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 | |
| 重庆市A级旅游景区名单 | 重庆市文化和旅游发展委员会 | |
| 一村一品示范村 | 重庆市农业农村委员会官网 | |
| 交通网络数据 | OpenStreetMap平台(https://master.apis.dev.openstreetmap.org/) | |
| 区县年均接待旅游人数、收入、 旅游资金扶持金额 | 2023年重庆市各区县统计年鉴 | |
表2 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Table 2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tourism resources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
| 目标层 | 准则层 | 要素层 | 指标内涵解释 | 单位/属性 | 权重/% | |
|---|---|---|---|---|---|---|
| 传统村落旅游资源评价A1 | 资源优势B1 | 乡土景观 价值C1 | 村落久远度D1 | 现存最早建筑修建年代 | 赋值/+ | 0.389 |
| 传统建筑规模D2 | 传统建筑占地面积 | hm2/+ | 1.818 | |||
| 传统建筑丰富度D3 | 建筑功能种类(祠堂、庙宇、书院等) | 个/+ | 7.090 | |||
| 民居独特性D4 | 反映地方特色的建筑形式 | 赋值/+ | 0.496 | |||
| 民居材料独特性D5 | 反映地域特性、文化、审美的建筑材料装饰 | 赋值/+ | 1.626 | |||
| 特色农业资源D6 | 以村落“一村一品”品牌数为表征 | 个/+ | 1.695 | |||
| 历史文化 价值C2 | 民俗活动丰富度D7 | 反映地方特色民俗活动次数 | 次/年/+ | 3.263 | ||
| 非遗文化传承度D8 | 非遗文化传承人人数 | 人/+ | 3.359 | |||
| 非遗文化稀缺度D9 |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等级 | 赋值/+ | 4.653 | |||
| 少数民族多样性D10 | 村落少数民族种类 | 种/+ | 4.611 | |||
| 原居民保留度D11 | 常住人口占村域户籍人口比 | %/+ | 0.689 | |||
| 历史文化多样性D12 | 历史演变中形成的村落类型(农耕型、 商贸型、军事型)及转型个数 | 种/+ | 0.409 | |||
| 历史文化地域性D13 | 村落所属文化区(库区文化、巫文化、 巴文化) | 赋值/+ | 12.343 | |||
| 环境特征B2 | 自然特征C3 | 环境舒适度D14 | 年均气温 | 赋值/+ | 0.486 | |
| 环境安全性D15 | 地质灾害危险性 | 无量纲/- | 0.129 | |||
| 森林资源和绿化水平D16 | 植被覆盖率 | 无量纲/+ | 0.345 | |||
| 生物多样性水平D17 | 生境质量指数 | 无量纲/+ | 0.690 | |||
| 社会特征C4 | 特色美食地域性D18 | 地方特色美食非遗小吃个数 | 个/+ | 2.359 | ||
| 乡风文明建设水平D19 | 村落所获的文明村、重点旅游村、美丽 宜居村庄等荣誉称号等级 | 赋值/+ | 14.902 | |||
| 基础设施完善程度D20 | 基础设施个数 | 个/+ | 10.172 | |||
| 经济特征C5 | 特色产业延续状态D21 | 传统特色产业个数 | 个/+ | 10.875 | ||
| 人均GDP水平D22 | 村民人均GDP值 | 元/+ | 4.725 | |||
| 开发条件B3 | 可达性 C6 | 区位对外连通程度D23 | 距离A级旅游景区距离 | km/- | 0.400 | |
| 交通对外联通程度D24 | 距过境道路距离 | km/- | 1.856 | |||
| 文化对外联通程度D25 | 潜在的非遗文化传承人人数 | 人/+ | 2.405 | |||
| 产业发展 水平C7 | 旅游接待水平D26 | 区县年均接待游客人数 | 万人/+ | 0.811 | ||
| 旅游收入水平D27 | 区县年均旅游收入 | 亿元/+ | 0.541 | |||
| 资金支持水平D28 | 区县旅游资金扶持金额 | 万元/+ | 1.184 | |||
| 市场潜力C8 | 潜在旅游者人数D29 | 一小时旅游圈客源市场常住人口数 | 人/+ | 3.776 | ||
| 潜在旅游者收入 和消费水平D30 | 一小时旅游圈客源市场人均可支配收入 | 元/+ | 1.903 | |||
表3 定性指标分级赋值方法Table 3 Qualitative index grading assignment method |
| 指标 | 定性指标赋值 | ||||
|---|---|---|---|---|---|
| 1 | 2 | 3 | 4 | 5 | |
| 村落建筑久远度D1 | 建国至1980年 | 民国 | 清代 | 明代 | 明代以前 |
| 民居独特性D4 | 普通中式建筑 | 地方特色建筑 | |||
| 民居材料地域性D5 | 石质 | 青砖 | 黏土砖 | 木 | 竹 |
| 非遗文化稀缺度D9 | 无 | 市级 | 省级 | 国家级 | 世界级 |
| 历史文化地域性D13 | 无 | 一种 | 多种 | ||
| 环境舒适度D14 | ≥35, < -5 | [29, 35), [-5, 7) | [22, 29), [7, 15) | [15, 22) | |
| 乡风文明建设水平D19 | 无 | 市级 | 省级 | 国家级 | 多个国家级 |
表4 阻力因子及赋值[34]Table 4 Resistance factors and assignments |
| 阻力因子 | 亚类 | 阻力值 |
|---|---|---|
| 道路等级 | 国道 | 45 |
| 省道 | 60 | |
| 县道 | 80 | |
| 乡道 | 120 | |
| 其他道路 | 180 | |
| 无道路 | 720 | |
| 坡度/(°) | 0~5 | 720 |
| 5~15 | 1080 | |
| 15~25 | 1800 | |
| >25 | 3000 | |
| 海拔/m | 0~500 | 720 |
| 500~1500 | 900 | |
| 1500~2500 | 1080 | |
| >2500 | 1800 |
表5 共生环境成熟度评价指标体系Table 5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maturity (%) |
| 旅游要素 | 指标内涵 | 权重 |
|---|---|---|
| 食 | 餐馆、小吃快餐店、甜品店、茶馆、咖啡厅 | 18.127 |
| 住 | 星级酒店、旅馆、青旅、民宿 | 12.921 |
| 行 | 加油站、加气站、充电站、停车场、汽车维修汽车租赁 | 16.769 |
| 游 | 旅游景点、红色旅游景点、纪念馆、动植物园、水族馆、宗教景点 | 9.066 |
| 购 | 购物中心、商业街、超市、便利店、市场 | 14.424 |
| 娱 | 度假区、游乐场、电影院、剧场、露营地、酒吧、棋牌室 | 14.411 |
| 医 | 综合医院、专科医院、急救中心、诊所、药店 | 14.282 |
表6 传统村落旅游共生系统分类分级Table 6 Classification and grading of traditional village tourism symbiosis system |
| 共生系统类型 | 示意图 | 特征 | 共生优势 | 共生环境 | 等级 |
|---|---|---|---|---|---|
| 文化遗产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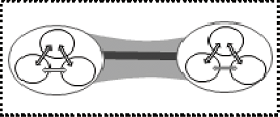 | ① 共生单元旅游资源价值高 ② 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丰富 ③ 建筑、非遗技艺、民俗节庆彰显文化吸引力与核心竞争力 | 内共生 优势型 | 成熟度高 | 重点 |
| 成熟度低 | 一般 | ||||
| 生态景观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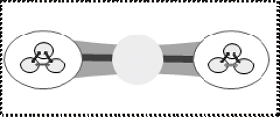 | ① 共生单元旅游资源吸引力欠缺 ② 外部有机体(景区、生态资源)资源禀赋强 ③ 共生单元与生态环境深度互动,融入生态旅游产业链,增值生态文化价值 | 外共生 优势型 | 成熟度高 | 重点 |
| 成熟度低 | 一般 | ||||
| 生态文化综合 开发型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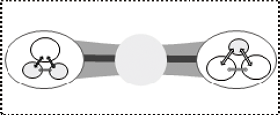 | ① 共生单元旅游资源价值较高,文化保护力度不够 ② 外部有机体(景区、生态资源)竞争力不足 ③ 共生系统内外共生关系互补融合,可提高传统村落旅游业抗风险能力,实现区域整体开发 | 内外共生 优势型 | 成熟度高 | 重点 |
| 成熟度低 | 一般 |
表7 重庆市传统村落共生环境各要素评价Table 7 Evaluation of each element of symbiotic environment of traditional villages in Chongqing |
| 食 | 住 | 行 | 游 | 购 | 娱 | 医 | 综合值 | |
|---|---|---|---|---|---|---|---|---|
| 均值 | 0.058 | 0.070 | 0.058 | 0.099 | 0.072 | 0.058 | 0.076 | 0.068 |
| [1] |
吴泓, 顾朝林. 基于共生理论的区域旅游竞合研究: 以淮海经济区为例. 经济地理, 2004, 24(1): 104-109.
[
|
| [2] |
熊海峰, 祁吟墨. 基于共生理论的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策略研究: 以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为例. 同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1(1): 40-48.
[
|
| [3] |
吴茂英, 张镁琦, 王龙杰. 共生视角下乡村新内生式发展的路径与机制: 以杭州临安区乡村运营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8): 2097-2116.
[
|
| [4] |
冯骥才. 传统村落的困境与出路: 兼谈传统村落是另一类文化遗产. 民间文化论坛, 2013, (1): 7-12.
[
|
| [5] |
程叶青, 胡守庚, 杨忍, 等. 面向乡村振兴的中国传统村落保护与利用: 挑战与展望.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8): 1735-1759.
[
|
| [6] |
王彩彩, 袭威, 徐虹, 等. 乡村旅游开发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 基于共生视角的分析.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35-356.
[
|
| [7] |
朱鹤, 高翔宇, 张生瑞, 等. 旅游资源区域组合: 内涵、识别技术与关键问题.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39(7): 1493-1511.
[
|
| [8] |
许春晓, 佘白连. 旅游目的地间共生的市场驱动机制研究. 旅游学刊, 2016, 31(7): 96-105.
[
|
| [9] |
许春晓, 周雪莲. 古村古镇群旅游共生发展新探: 基于怀化中部古村古镇群案例的技术方案. 旅游论坛, 2018, 11(6): 71-80.
[
|
| [10] |
|
| [11] |
|
| [12] |
卢佳辰, 刘爱利. 传统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发展的共生模式研究: 以江西省寒信村为例. 资源科学, 2023, 45(7): 1396-1409.
[
|
| [13] |
李伯华, 易韵, 窦银娣, 等. 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三生”融合的系统动力学机制研究: 以湖南德夯村为例. 地理科学进展, 2024, 43(3): 517-530.
[
|
| [14] |
高长征, 付晗, 龚健. “文化驱动”视角下传统村落共生发展路径研究: 以河南浚县5个传统村落为例. 地域研究与开发, 2021, 40(2): 169-173, 180.
[
|
| [15] |
杨馥端, 窦银娣, 易韵, 等. 催化视角下旅游驱动型传统村落共同富裕的机制与路径研究: 以湖南省板梁村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2): 357-374.
[
|
| [16] |
|
| [17] |
|
| [18] |
龙彬, 宋正江, 赵耀. 重庆传统村落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小城镇建设, 2020, 38(4): 72-81.
[
|
| [19] |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2022年重庆市生态环境状况公报. 2023.
[Chongq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Bureau. Bulletin of Chongqing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2022. 2023.]
|
| [20] |
重庆市统计局. 重庆市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第二号). 2021
[Chongqing Bureau of Statistics. The seventh national census bulletin of Chongqing (No.2). 2021.]
|
| [21] |
重庆市统计局. 2022年重庆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2023.
[Chongqing Municipal Bureau of Statistics. Statistical bulletin of Chongqing's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2022. 2023.]
|
| [22] |
刘红梅, 王刚. 基于发生学与实践的传统村落时空演变过程及机制: 以重庆市为例.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022, 31(1): 59-72.
[
|
| [23] |
荣慧芳, 陶卓民, 李涛, 等. 基于网络数据的苏南乡村旅游客源市场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20, 36(6): 71-77.
[
|
| [24] |
杨坤, 芮旸, 李宜峰, 等. 基于共生理论的中国特色保护类村庄振兴类型细分研究.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11): 1861-1875.
[
|
| [25] |
陈建波, 明庆忠. 基于改进层次分析法的健康旅游资源评价研究. 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 2018, 34(4): 69-73.
[
|
| [26] |
李悦铮, 牟方元, 梁娟. 湿地旅游资源评价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经济地理, 2019, 39(1): 192-197.
[
|
| [27] |
汪侠, 顾朝林, 刘晋媛, 等. 旅游资源开发潜力评价的多层次灰色方法: 以老子山风景区为例. 地理研究, 2007, 26(3): 625-635.
[
|
| [28] |
|
| [29] |
魏峰群, 马文硕, 杨蕾洁. 传统村落活态化价值认知与多维弹性评估模型研究: 基于陕北地区案例实证. 地理科学进展, 2023, 42(4): 701-715.
[
|
| [30] |
唐承财, 刘亚茹, 万紫微, 等. 传统村落文旅融合发展水平评价及影响路径. 地理学报, 2023, 78(4): 980-996.
[
|
| [31] |
王淑佳, 孙九霞. 中国传统村落可持续发展评价体系构建与实证. 地理学报, 2021, 76(4): 921-938.
[
|
| [32] |
程启月. 评测指标权重确定的结构熵权法. 系统工程理论与实践, 2010, 30(7): 1225-1228.
[
|
| [33] |
陈瑾, 赵超超, 赵青, 等. 基于MSPA分析的福建省生态网络构建. 生态学报, 2023, 43(2): 603-614.
[
|
| [34] |
叶随, 席建超. 青藏高原区旅游廊道识别与评价. 地理学报, 2023, 78(10): 2630-2644.
[
|
| [35] |
高宇, 木皓可, 张云路, 等. 基于MSPA分析方法的市域尺度绿色网络体系构建路径优化研究: 以招远市为例. 生态学报, 2019, 39(20): 7547-7556.
[
|
| [36] |
中国旅游研究院. 中国国内旅游发展报告(2023—2024). 2024.
[China Tourism Academy. Report on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tourism in China(2023-2024). 2024.]
|
| [37] |
邱海莲, 由亚男. 旅游廊道概念界定. 旅游论坛, 2015, 8(4): 26-30.
[
|
| [38] |
薛乾明, 黄跃昊, 邓清文, 等. “文荫武备”理念下陇中黄土高原传统村落的活化及治理研究: 以榆中县黄家庄村为例. 地理研究, 2024, 43(6): 1591-1610.
[
|
| [39] |
康晨晨, 黄晓燕, 夏伊凡. 传统村落文化遗产价值分级分类评价体系构建及实证: 以陕西省国家级传统村落为例.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23, 51(2): 84-96.
[
|
| [40] |
潘颖, 邹君, 刘雅倩, 等. 乡村振兴视角下传统村落活态性特征及作用机制研究. 人文地理, 2022, 37(2): 132-140, 192.
[
|
| [41] |
|
| [42] |
胡赛强, 杨迪, 刘淑虎. 福建省传统村落空间格局及历史演变. 经济地理, 2024, 44(9): 211-220.
[
|
| [43] |
李伯华, 程波, 窦银娣. 湘西侗族传统村落图式语言解析与修复路径研究. 地理学报, 2025, 80(3): 828-850.
[
|
| [44] |
陈晓艳, 黄睿, 洪学婷, 等. 传统村落旅游地乡愁的测度及其资源价值: 以苏南传统村落为例. 自然资源学报, 2020, 35(7): 1602-1616.
[
|
/
| 〈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