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组织关系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框架与网络形式
|
李秋芳(1996- ),女,河南周口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研究。E-mail: l_qf@webmail.hzau.edu.cn |
收稿日期: 2023-08-14
修回日期: 2023-12-13
网络出版日期: 2024-04-11
基金资助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72274074)
国家自然基金项目(71774065)
A logical framework and network form of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an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 perspective
Received date: 2023-08-14
Revised date: 2023-12-13
Online published: 2024-04-11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整合多方资源要素、协调多元主体行动、提升整治效率提供了有效路径。从组织关系视角构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框架,以湖北省J县GQ镇为例,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包含命令传递、资源流动和信息沟通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并分析网络结构特征,采用指数随机图模型剖析这些网络的内外生机制。结果显示:(1)案例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中三个网络密度较低,尚未形成紧密联系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体系;(2)命令传递网络和资源流动网络具有典型的“核心—边缘”结构和“小世界”特征,存在以县政府、镇政府为中心的命令传递集群和以施工企业为中心的资源流动集群,大量农村集体和村民位于网络边缘未发挥主体作用;(3)三个网络的形成不同程度上受互惠性、核心—边缘结构效应、传递闭合效应、连通效应等内生机制和主体属性、夹带效应等外生机制的影响。据此提出,为提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有效性,应强化核心主体的稳定作用,搭建多元化参与渠道,发挥农村集体和村民的内生动力。
李秋芳 , 汪文雄 , 崔永正 , 陈丹玲 . 组织关系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的逻辑框架与网络形式[J]. 自然资源学报, 2024 , 39(4) : 912 -928 . DOI: 10.31497/zrzyxb.20240410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multiple subjects is an inevitable requirement to promot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contex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t is also an effective path to integrate multiple resource elements, coordinate the actions of multiple subjects, and improve governance efficiency. This article first constructs a logical framework for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rganizational relationships. Using G twon, J county, Hubei province as a case study, this research constructs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through social network analysis, covering command transmission, resource flow, and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It then examines the network's structural features and employs exponential random graph models to explore the networks' underlying mechanisms, both internal and external.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The density of the three networks in th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in the case area is low, and a closely connected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has not yet been formed. (2) The command delivery network and resource flow network have a typical "core-edge" structure and "small world" characteristics. There are command delivery clusters centered on county governments and town governments, and resource flow clusters centered on construction enterprises.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collectives and villagers are located on the edge of the network and do not play a major role. (3) The formation of the three networks is affected to varying degrees by endogenous mechanisms such as reciprocity, core-periphery effects, transitive closure effects, and connectivity effects, as well as exogenous mechanisms such as subject attributes and entrainment effects.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hat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by multiple subjects in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the stabilizing role of core subjec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channels should be built, and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rural collectives and villagers should be brought into play.
表1 GQ镇全域土地综合整治项目参与主体Table 1 Participants in the comprehensive land consolidation project in GQ town |
| 主体属性 | 参与主体 | 主体属性 | 参与主体 |
|---|---|---|---|
| 政府及其职能部门 | J县人民政府(A1) | 金融机构 | 中国农业银行湖北XN分行J县支行(C1) |
| J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A2) | 农村集体 | 村委会:ZS村(D1)、SGL村(D2)、LH村(D3)、GN村(D4)、G村(D5) | |
| J县农业农村局(A3) | |||
| J县水利与湖泊局(A4) | 村理事会:ZS村(D6)、SGL村(78)、LH村(D8)、GN村(D9)、G村(D10) | ||
| J县林业局(A5) | |||
| XN市生态环境局嘉鱼县分局(A6) |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ZS村(D11)、SGL村(D12)、LH村(D13)、GN村(D14)、G村(D15) | ||
| J县交通运输局(A7) | |||
| J县发展和改革局(A8) | 村民 | 各村村民代表:ZS村(D16)、SGL村(D17)、LH村(D18)、GN村(D19)、G村(D20) | |
| J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A9) | |||
| J县文化和旅游局(A10) | 其他社会组织 | WHYDLC设计工程有限公司(E1) | |
| J县财政局(A11) | SHLZ城市规划设计事务所(E2) | ||
| GQ镇政府(A12) | WH市规划研究院(E3) | ||
| 企业组织 | J县城镇建设投资有限公司(B1) | ND建筑设计事务所有限公司(E4) | |
| J县投资建设公司(B2) | ZJYC空间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E5) | ||
| G村集体企业(B3) | 专家及研究机构(F1) |
表2 ERGM变量说明Table 2 Description of ERGM variables |
| 效应 | 示意图 | 含义 | 效应 | 示意图 | 含义 |
|---|---|---|---|---|---|
| 边(edges) |  | 最基础的网络结构,网络 密度的间接反映 | 多连通性 (gwdsp) |  | 参与主体通过多路径传递协同治理关系的趋势 |
| 互惠性 (mutual) |  | 网络中主体之间相互依赖 形成互惠关系的倾向 | 传递闭合性 (gwesp) |  | 三元组关系的传递闭合趋势 |
| 聚敛性 (gwidegree) |  | 某一主体接受网络关系数 量的分布趋势 | 同质性 (group)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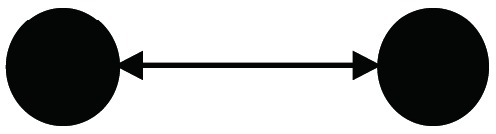 | 网络中主体属性的影响 |
| 扩散性 (gwodegree) |  | 某一主体发出网络关系数 量的分布趋势 | 夹带效应 (edgecov) |  | 不同类型的关系与所观测关系的联系 |
表3 协同治理网络的描述性统计特征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
| 网络基本特征 | 网络关系数/个 | 网络密度 | 平均路径长度 | 平均聚类系数 |
|---|---|---|---|---|
| 命令传递 | 110 | 0.064 | 1.934 | 0.348 |
| 资源流动 | 127 | 0.074 | 2.240 | 0.355 |
| 信息沟通 | 491 | 0.285 | 1.847 | 0.553 |
图3 多元主体协同治理网络拓扑图注:原图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tF9jpOD0Dutv3AkwwqLhoA?pwd=9dr8. Fig. 3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network topology |
图4 网络社群结构注:原图链接为 https://pan.baidu.com/s/1wbqAzby8Q4VjWYYCT8-pzQ?pwd=pbaj. Fig. 4 Network local structure |
表4 ERGM回归结果Table 4 ERGM regression results |
| 变量 | 命令传递网络 | 资源流动网络 | 信息沟通网络 |
|---|---|---|---|
| edges | -3.3865*** (0.3124) | -4.9760*** (0.3846) | -20.1028** (2.9670) |
| mutual | 0.5143*** (0.4050) | 3.1718*** (0.2321) | |
| gwidegree | 0.3349*** (0.5298) | -2.8476*** (0.5696) | |
| gwodegree | -3.0815*** (0.5291) | 1.1637* (0.6489) | |
| gwdsp | -0.2960*** (0.0547) | 0.0517 (0.0406) | |
| gwesp | 0.5324*** (0.2119) | 0.3706* (0.1926) | 13.1632*** (2.3167) |
| group | -0.7739*** (0.2766) | -0.4199* (0.2349) | 0.9768*** (0.1091) |
| edgecov.ml | 2.8272*** (0.2824) | 2.2831*** (0.3086) | |
| edgecov.xx | 2.2876*** (0.3142) | 2.3362*** (0.3161) | |
| edgecov.zy | 2.6788*** (0.2977) | 2.1757*** (0.3090) | |
| AIC | 458.5 | 526.3 | 1108 |
| BIC | 502.1 | 575.4 | 1141 |
注:***、**、*分别表示双尾检验中0.1%、1%和5%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标准误。 |
| [1] |
金晓斌, 罗秀丽, 周寅康. 试论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基本逻辑、关键问题和主要关系.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11): 1-12.
[
|
| [2] |
韩博, 金晓斌, 顾铮鸣, 等. 乡村振兴目标下的国土整治研究进展及关键问题. 自然资源学报, 2021, 36(12): 3007-3030.
[
|
| [3] |
汤瑜, 于水.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线性轨迹、逻辑框架与实践反思.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21, 43(6): 109-116.
[
|
| [4] |
范业婷, 金晓斌, 张晓琳, 等. 乡村重构视角下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的机制解析与案例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4): 109-118.
[
|
| [5] |
MARCH H A S A G. Organizations (2nd Edition). New York: Wiley-Blackwell, 1993.
|
| [6] |
魏江, 刘嘉玲, 刘洋. 新组织情境下创新战略理论新趋势和新问题. 管理世界, 2021, 37(7): 182-197, 13.
[
|
| [7] |
王涛. 组织跨界融合: 结构、关系与治理. 经济管理, 2022, 44(4): 193-208.
[
|
| [8] |
曹海军, 陈宇奇. 部门间协作网络的结构及影响因素: 以S市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试点为例.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2022, 11(1): 145-156.
[
|
| [9] |
|
| [10] |
|
| [11] |
|
| [12] |
|
| [13] |
文军, 陈雪婧. 社区协同治理中的转译实践: 模式、困境及其超越: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分析. 社会科学, 2023, (1): 141-152.
[
|
| [14] |
石峡, 朱道林, 张军连. 土地整治公众参与机制中的社会资本及其作用. 中国土地科学, 2014, 28(4): 84-90.
[
|
| [15] |
姜棪峰, 龙花楼, 唐郁婷. 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土地利用多功能性视角. 地理科学进展, 2021, 40(3): 487-497.
[
|
| [16] |
|
| [17] |
梁伟. 农地细碎化的协同治理模式: 以皖南繁昌区为例. 中国土地科学, 2022, 36(10): 100-108.
[
|
| [18] |
|
| [19] |
刘建生, 党昱譞, 惠梦倩. 土地整治项目协同治理: 理论框架与案例研究. 中国土地科学, 2016, 30(11): 61-67.
[
|
| [20] |
孙婧雯, 陆玉麒. 城乡融合导向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机制与优化路径. 自然资源学报, 2023, 38(9): 2201-2216.
[
|
| [21] |
董祚继, 韦艳莹, 任聪慧, 等. 面向乡村振兴的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创新: 公共价值创造与实现. 资源科学, 2022, 44(7): 1305-1315.
[
|
| [22] |
周小平, 申端帅, 谷晓坤, 等. 大都市全域土地综合整治与耕地多功能: 基于“情境—结构—行为—结果”的分析. 中国土地科学, 2021, 35(9): 94-104.
[
|
| [23] |
于水, 汤瑜. 全域土地综合整治: 实践轨迹、执行困境与纾解路径: 基于苏北S县的个案分析. 农业经济与管理, 2020, (3): 42-52.
[
|
| [24] |
|
| [25] |
任浩, 甄杰. 管理学百年演进与创新: 组织间关系的视角. 中国工业经济, 2012, (12): 89-101.
[
|
| [26] |
|
| [27] |
|
| [28] |
|
| [29] |
|
| [30] |
|
| [31] |
张凌媛, 吴志才. 乡村旅游社区多元主体的治理网络研究: 英德市河头村的个案分析. 旅游学刊, 2021, 36(11): 40-56.
[
|
| [32] |
何奇龙, 唐娟红, 罗兴, 等. 政企农协同治理农业面源污染的演化博弈分析. 中国管理科学, 2023, 31(7): 202-213.
[
|
| [33] |
高强, 周丽. 协同治理视阈下乡村建设实践样态解析: 基于江苏常熟“千村美居”工程的案例观察.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2, 22(6): 22-33.
[
|
/
| 〈 |
|
〉 |